

「一群“大笑着的痊愈者”告诉我们,你怎么生活,女性就怎么生活。」
出现了这么一部电影。
有人说它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弗兰西丝·哈》”,有人说它“早该来了”,有人看了之后说“我们以后要更多的小妞电影大妞电影大妈电影奶奶电影!”,也有人觉得它像走在路上突然递过来的一片巨大的创可贴,暖得让人一时间不知道该贴在哪里好。
11月22日,邵艺辉编剧、导演、剪辑指导的电影《好东西》正式上映,豆瓣开分9.1,截至目前票房突破5亿。《好东西》描摹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女儿“小孩儿”王茉莉搬到新家后,和邻居小叶一同经历的故事,有笑也有泪。
王铁梅,王茉莉,小叶,这群带着各自或新或旧创伤的女性角色们,跨过了城市和生活的空间,亲手捏造着宽容浪漫的新新宇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属于“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人的世界。

(《好东西》片段)
01
以创伤写作,用疼痛共时
《好东西》虽然给大家的整体印象是轻盈灵动的,是清空草稿箱般的“废话电影”,但它也并不那么松弛,那么无伤大雅,这其实是一个用创伤编织出的故事。
王铁梅的创伤是他人的期待。作为一个母亲,社会的传统目光期待她在家庭做忠贞的守卫者而不能对此感到厌烦,但王铁梅迈出厨房,走入了生产和劳动的领域,追求事业理想,把自己作为方法,言说着同类群体的民族志。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作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小马期待能和她“周末一起看个电影”,她直言“我们不是能一起看电影的关系,你走吧”。
作为一个女性,她没有顺应大众文化语境中对女人的期待。《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中指出,现存的霸权主义的文化语境将“抽烟”等归类为具有“男性气质”的行为,男性们通过这套话语凝成共识,找到群体。
综艺《思想验证区域》中有通过“一起抽一支”而建立起来的男性共同体“吸烟角”;《认识的哥哥》中金希澈用香烟作为段子调笑女嘉宾,如果女艺人同意吸烟则是“很会玩”;电影《后会无期》用三位男性角色在路边一起随地小便的场景作为剧照——此先存在一套用于区分的话语,代表着一种共识的期待,人为地将“女”和“男”割裂开来,如同用文明来定义疯癫一般暴力傲慢。

(综艺《思想验证区域》“吸烟联盟”与电影《后会无期》海报)
而王铁梅回溯到了在区分还未成立的时刻,以母性和人性包孕了这种不应如此的分裂——她一边抽烟一边写作,她说脏话也说“对不起”,她呵斥路边随地小便的男人,她说“淑女这词儿早该过时了”,她潇洒,也困窘,她有新闻理想,也能“做一百零八种面”。
她自我解脱于这种来自期待的微妙的暴力,用冒犯的姿态活着。如同那道横亘在小腹的疤痕,连绵的,颗粒的,滔滔生活的。

(王铁梅抽烟、装灯泡、修空调)
小叶的创伤是在原生家庭里缺爱的人一生都在他人身上寻求认同。她投入现代都市的约会文化之中,在一遍遍快准狠的痛苦中找寻确定性和安全感,在不断追问“无条件的爱”的过程中强迫性重复着熟悉的创伤路径。她不敢正视爱欲的死亡,她在湍急的河中奋力呼救。
“王茉莉们”的创伤是“抓娃娃”。电影中的王茉莉被养育为一个十分理想的全然的“自然人”,有着几乎超出年龄的哲思和闭环自洽的价值观,不会轻易被拖拽进任何叙事。世界在她面前是敞开的、待走入的,她在无主的游乐园进出自由。

(王茉莉的《记一次难忘的旅行》手抄报)
然而,现实中的“王茉莉”们,却似乎正在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各种培养模式和教育赛道。各种特长生招生渠道,“双减”之后在城市各个角落深处隐秘滚动的补习班,制造谷爱凌和郑钦文的幻梦……
父母们过于膨胀的自我蔓延到了孩子的世界。如果一个生命被诞生到世上之后从此作为一个指标,一类投射,一套计划,一个观众,那他们一生都没有被看见,那他们一生都只会在台下鼓掌,一遍遍留着泪却从没有尝到过泪的咸。

(蓝佩嘉《做父母,做阶级:亲职叙事、教养实作与阶级不平等》)
《好东西》描述的三代或三类女性——王铁梅、小叶、王茉莉,昭示着自我的创伤,小心翼翼地用只有彼此能听懂的暗语互相试探,触碰,拥抱。
正如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将南斯拉夫解体的历史写作一本《疼痛部》。在书中,主人公来自一个已经解体、不复存在的国度,以“前南斯拉夫流民”的身份来到荷兰的一个学校成为了语言教师,负责教授南斯拉夫解体前的官方用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一门已经不存在的语言,一群已经无处求证的身份。书中的角色们因为很庞大的原因骤然被抛掷出了先验的属地,失去了国家和语言,成为了文化意义上的流民,缝隙中间的人。
于是,他们不得不开启了流浪的经历,在新鲜的人群中用陈旧的语言——一套如今已经失去意义的、空虚的流通货币——来打暗号似的确认彼此的身份,建立隐秘的共同体。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疼痛部》)
王铁梅、小叶、王茉莉,她们有着她们的“疼痛部”和独特的“语言”。她们微小而具体,没有满足各种“期待”,她们都是宏大叙事中的流民。
因此她们游离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用这种共时性的疼痛与彼此、与观众之间创造了一场编码与解码的游戏:家务劳动、母职惩罚、月经痛经……哪怕是地铁上一闪而过的一本红色封皮的书,这些都成了暗语,在贯穿第四堵墙的相遇之时,邀请你与她们一同在此地,漫游,标记,筑巢。

(王铁梅在地铁上看的书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02
赋魅的空间与漫游者
《好东西》里除了人的创伤,还有城市的创伤。
故事的发生地,上海,一座在当今语境下与“精英文化”“小资”等标签强关联的城市,它愈发被中产外溢的生活方式填满和取代,被解读着,被遗失着。
《好东西》看见了现代都市的另一侧切,将其再次“赋魅”。破旧的洋房,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屋内囤积的生活物资和阳台上的“菜园”,唱着“明天会更好”的青年人,进行自我表达的万圣节……不是现象和表演的堆砌,而是内窥式地呈现。

(《好东西》对城市集体记忆的再现)
它们如同美国在“9·11”事件之后蔓延开来的脱口秀艺术,如同19世纪巴黎城市中通过行走进行反抗的漫游者。它们只是存在着,就构成一种沉默和对抗,对抗现代性的重力,对抗机械呆板的城市经验,对抗都市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与悖谬性,在公共空间的每一处留下无可回避的痕迹。
除了狭义的实体的空间,《好东西》电影里最高光时刻的一段——王铁梅的日常家务劳动与自然世界的声音蒙太奇。这个片段用充满浪漫和想象的手法呈现了一个女性日常的生活空间,并将其与自然空间关联。
平常变得神圣,隐匿走向看见,细碎进而磅礴。母亲亲手创造着我们与世界的脐带。这是电影对漠视家务劳动的诗性反抗与浪漫重建。

(《好东西》中的声音蒙太奇片段)
就像朗西埃提出的“歧感”及其共同体的感念,这种基于空间的叙事形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对规训和共识的扰乱,在断裂之处无目的绽开。也如书籍《疼痛部》中所说,这是一群“大笑着的痊愈者”。
03
娜拉出走之后,仍然不想放手
《好东西》笑着闹着流泪着,有种“我们就讲这个了”的冲劲儿,让人望着上海夏天被晒起一个卷儿的树叶微醺,但走出电影院,手机消息一响,踏上漫长的地铁,看看身旁的男人们,人们就会发现自己面前的生活怎么那么棘手异常——这是这部电影“泡泡感”和割裂感的一部分。
《好东西》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略有悬浮,太过理想,稍显僵硬地去追求着属于“可能性”的左派叙事。
在这儿单亲妈妈可以转圜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因为要接送孩子而自由地离开工位,对自己的文章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在这儿一个兼职乐队主唱的修音师女孩儿能租下上海徐汇的房子,并且主动发起着一段“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能当一天她的妈妈吗?”的邻里关系。
在这儿公立小学的语文老师不会在意学生的缺勤和课堂小动作,能够读懂并且鼓励她“我不是富二代,我不再幻想了”的自由写作,还锋利地质问着“谁教你的举报?”。
在这儿男人愿意为了取悦你来“表演女权”,可现实中就算有可以对照的男性形象也都是他们三个的“平替+黑化”版本。
在这儿小孩儿真的可以从容自然地不进“第一梯队”,可难免让人思考这种如此解构的教育观念下的小孩在当下社会的来路和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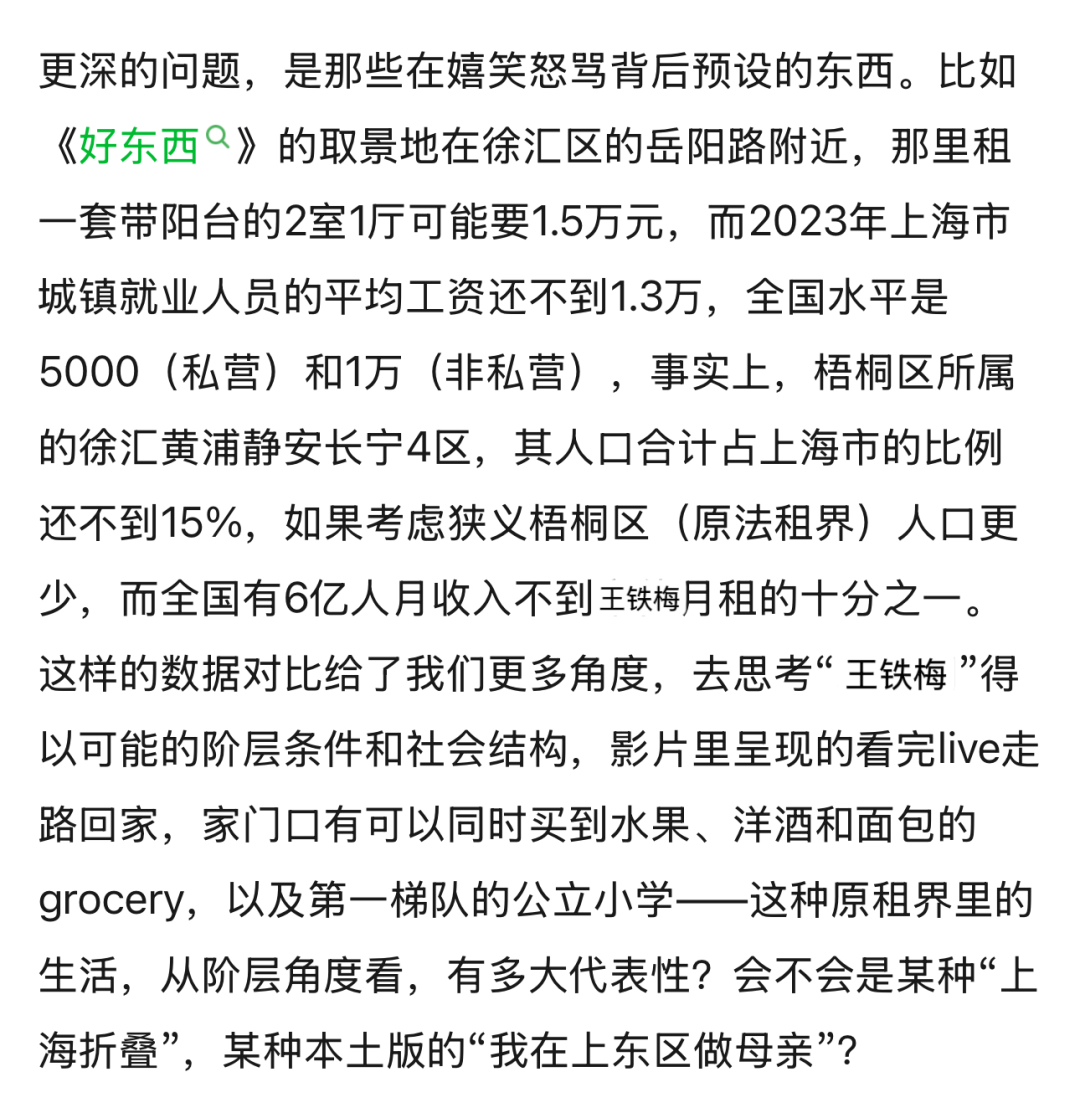
(豆瓣《好东西,坏未来》影评节选)
《好东西》是离不开精英叙事和共情门槛的好东西。主角们过着小红书式的生活,说着脱口秀一样的金句,穿着具有文化隐喻的t恤衫。就如同在电影中以“咱们别什么都扯女性话题啊”话术来贩卖《看不见的女性》一样,这部电影或多或少是符号的缝合,“表演艺术家”们未来几年的时尚单品,同温层之间的谜语。
真正需要用这部电影的主旨思想去改造自己生活的人或许是没有机会看到或者看懂它的,但或许,这也正是女性主义思想普遍下沉中必经的一环。“娜拉”们出走之后,回头冲我们招手。
德勒兹说艺术不是再现现实,而是创造一种尚未存在的新现实。正是《好东西》这种大胆不羞耻的理想主义色彩,召唤着我们相信未来,相信相信的力量,想象一种新的男女形象,一种新的育儿组合,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生活方式。

(微博网友@老袁circle 对于《好东西》创造新秩序的探讨)
《好东西》仿佛在说,我们在这儿拔地而起了一个新的文明,我们要创造一个玩儿着新的游戏的世界,在这里没有男人和马,没有车子票子,没有父和父的父,只有我爱你,对不起,和没关系。
小叶告诉王茉莉“你怎么打鼓,女孩儿就怎么打鼓”。而这三位可爱生动的女性角色正坦诚地向你展示着伤疤,小动物一样摇着尾巴,她们告诉每一个知晓“好东西”为何物的人——你怎么生活,女性就怎么生活。活得或高亢,或低落,我多骄傲,这是我的骨架,我的内脏。
(图片素材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微博)编剧赵涟《 <好东西> ·波伏娃·人造子宫》
(播客)异见房间《马是男人的, <好东西> 是全人类的》
(播客)不合时宜《上海「变装」:一座城市的幽默、松弛和创伤》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